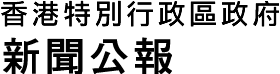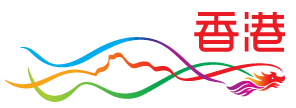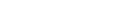财政司司长出席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六十周年院庆讲座致辞全文(只有中文)(附图/短片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大家好。今日很高兴来到中大参加联合书院这个聚会与大家见面,确实有很多同学在这里。
中大校园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之优美,我相信在这么好的环境读书,尤其是对一些宿生来说,一定是非常开心的。对我来说,读书的岁月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,尤其是离开家的那段时间。转眼间都差不多半个世纪,是相当长的时间。
首先很多谢联合书院的邀请,给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这个成长故事,一些加入政府三十年来的一些得着。我希望这个故事不是太沉闷。
好像刚才的介绍,我小时候(就读)喇沙小学,然后在喇沙(书院)。我在初中时读到十三岁就与我的家人一起移民美国,一家六口,当时我们住在 Manhattan(曼克顿),在八街,在Second Avenue和Third Avenue中间有一个名St. Mark's Place的地方居住。
我觉得那个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地方,因为在家对面有一个Discotheque(的士高)叫做Electric Circus。那时是很「型」的地方,全纽约最有「型」的人士每晚都在那里出现,以及那里有很多乐队整晚驻场(表演),如"Deep Purple","Jefferson Airplane"等等,每晚在该处玩是很「型」的。一、两个街口之外就是Fillmore East,差不多是全纽约最多音乐会的地方。然后,另一条街就有一个名为St. Mark's Theatre。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四毛钱可以看一天电影,电影是不停地放映,你可以进去坐下就可以看电影看一天,当时是四毛钱,当时是不算便宜的,四毛钱可以看一天电影是非常开心的。
我有三个弟妹,我们一家六口就在该处住了一段时期。家境不算富裕,我父母都是早出晚归,忙于生计。爸爸当时算很幸运,加入了当时在纽约一个钢铁工人的工会。因为在纽约,如果你不加入工会,很多工作都不能做。他加入了这个工会之后,在一间罐头公司做工,我母亲做车衣,其实他们的转变也不小,因为他们之前都是教师。去到纽约,很多方面跟香港不同,所以都要转变一下。所以我和弟妹那几年非常自由,因为他们很忙碌工作。虽然我们的物质稍为欠奉,但是过得非常开心,因为那段时间有绝对自由。
我高中亦都经过一个考试的取录过程,入读Stuyvesant High School。Stuyvesant High School在纽约是一间要考试才可入读的学校,但考试的过程是非常公道的,每一年收录720名学生,视乎你的成绩,考一个联合考试,成绩以720为界,(学校)收录(这个)分数以上的学生。当时在纽约来说,我那班同学差不多八成多是犹太人,有一成多是亚洲人,主要都是中国人;黑人、西班牙裔那些只得几位。但那段时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结交很多朋友,亦认识了很多不相同的文化,亦可以了解到多元的重要性和怎样尊重其他人的价值,更重要的一件事,是学习到怎样可以尊重自己,尊重自己的文化。
后来,读了几年后很幸运考上MIT(麻省理工学院),我当时很喜欢的是美术及工程,所以我选择读建筑Architecture。令我这段时间最深的印象,除了当时有很多示威活动外,就是每日都练习数小时剑击,在Fencing Room(剑击室)内花很多时间,其他时间整晚回到自己的Studio(工作室),那段时间真的不需要睡觉。在工作室创作,当时亦有很多外面的活动要求帮手制作不同的Poster (海报),我亦都帮别人制作很多Poster。当时我做silk screening(丝印)也颇到家的,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仪器可以拍照,我们都做得不错。整天晚上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、谈天和看书。我相信跟大家现在一样,晚上不用睡觉,可以有些时间,好似现在这样的聚会,就可以稍为休息一下。
当我毕业之后,我在一间建筑公司工作,派了我专门设计洗手间的细节,我做了数个月后,感到颇为不开心,就离开和另一些朋友合资开办了一间公司,从事装修。发觉和要求我们装修的人,都是按杂志上看到的,例如《Better Homes and Gardens》等杂志,要求你按着那样做,我也觉得不是太适合自己。
后来我亦有一段时间在唐人街一个名叫耆英会的组织,帮手参与洗地及扫地等,帮忙煮顿午饭,然后送饭之类的工作,亦都工作了一段时间。我亦在那段时间,用上自己少许建筑上的知识,在Basement(地库)建了一间小诊所。在诊所找一些医生朋友,以及护士朋友,当时亦劝当时的女朋友,即是现在的太太帮忙去营运,免费服务老人家。因为这个小诊所的存在,亦都推动整个社区建设第一个华人诊所。这个诊所至今仍在运作,我的太太亦在诊所工作。
一段时期后,我看到当时很多从香港移民来到Boston的学生,在读书上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,我就觉得或者我可以尝试一下教书,我就到去念了一个夜校的双语教育硕士学位,然后在Boston Public Schools,在公立学校内从事教书及行政工作,亦有机会从事课程规划上的工作。当时的工作亦相当具挑战性,薪酬亦不错。我当时和太太,和两名子女,都过着相当中产的生活。很多人问我,如果我当时过着这么中产的生活,你为何要回来香港呢?其实回来香港前,在美国居住了差不多二十年,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,要全家人到一个新环境,重新开始适应是不容易的。子女才只得两岁和六岁,当时我的外母亦责骂我,问我有一个舒适生活,这么安定,还要走到哪儿呢?
或者令到我有一个很大感受的,便是当时的中产生活确实是带我入了一个所谓的comfort zone,令整个人的惰性非常之大。我看看很多的朋友,像是(跌入)一个陷阱,突然发觉自己过了数十年也是过同一样的生活,我就对这方面有少少恐惧,担心自己都会跌入了这样的问题,所以就开始想一想,情况有什么可以改变呢?
在七十年代,其实在美国的种族矛盾相当深,少数族裔很多都受到歧视,当然自己也体会过,或者大家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也知,当时跟黑人你不能说「N」字,说「N」字会很大件事。对中国人来说,我们也很抗拒「C」字,说了「C」字便打架,那些「架」我也打得不少。其实,我在外地的生活,尤其是和我同一辈的移民朋友,很多华侨对自己国家的感情是相当强烈的,一些华侨都非常爱国。当时美国社会亦经常有这些学生示威、游行、集会、当时反对越战、争取平等、种族上的平等、公民权益,当时亦有保卫钓鱼台的运动,亦带起了不少大家对国家的情怀,我亦有参加不少这些活动。这些活动对我自己个人的成长,对我整个学习过程来说,都非常之好,对给我有个机会作出思考,对社会发展方面亦都可以了解多些。
在八十年代的初期,内地开始改革开放,香港亦面对不少前途问题,虽然当时有不少香港人开始移民到外国,但我就当时想,和太太谈过,很详细谈过,就觉得这是重要时刻,香港会有很多发展机会,我和太太和两个子女决定回香港工作,为香港做些事。我们在筹备时,太太到了Graduate School读了一个Nurse Practitioner(护理学的课程),有关老人科(geriatric)的工作。我亦考入了哈佛大学修读公共行政硕士,当时在哈佛,因缘际会认识了香港派来读书的曾荫权,他亦为我介绍了AO(政务主任)的工作。其实当时我亦有个Offer,就是一间国际学校成立,希望我去当校长的。当时我在衡量当一辈子校长好,还是回来考AO呢?两个我都有offer,我最后就决定回来做AO。AO的好处就是经常两、三年就可以转第二份工,一方面没有那么闷;另一方面亦可以学到多些东西、可以见识多些不同的事情,这方面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选择了,我亦觉这个是一个十分好的决定。这三十年来,对我来说都是在欢乐中度过。我回来香港第一个岗位就是沙田这里。我相信黄宏发都很记得,我认识他时他在District Board(区议会),我当时是助理专员。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城市广场当时刚刚开幕,当年也许大家都不知道,曾经「破天荒」在城门河放过烟花。这些是历史来的,街坊很开心,今日大家都未必可以想像得到。
不知道大家有否看过《点五步》这出戏?如果有的话,这个是讲「沙燕队」的故事。这是当时我们部门透过棒球来凝聚社区的一个措施。这出戏其实都不错,不过我觉得最大的缺点,是没有一个英俊的男演员来饰演当时的ADO(民政事务助理专员)。
之后我有不少工作是跟财金、经贸有关,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也不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在Securities Commission工作过,即证监会的前身,我在那里是担任过Securities Officer,负责加强对小投资者的保障。我也担任过当时的财政司司长翟克诚的政务助理,我亦被派过当彭定康的秘书,亦很近距离的见证香港回归那一段的历史。接着我就被派去伦敦经贸办事处,作为在伦敦的代表。然后董先生在一年两年后就要求我回来当海关关长。我那时组织一些专责的队伍打击翻版(光碟)的。我想在座有很多同学可能连那些翻版光碟也没有见过,代表我们有多成功。海关关长是我当主要官员的第一份工作。接着我也当过规划地政局局长、工商及科技局局长,刚才也介绍过,我亦都当过WTO(世界贸易组织)在香港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的主席。然后我当了特首办主任一段短的时间;然后○七年就开始做财政司,今年就是第十年。
八十年代到今日,的确我觉得是香港的大时代,我真的很有幸可以在这个大时代中看到香港的发展,我在政府的工作亦有机会见证不少重大的事件,更重要的就是,我觉得我可以帮到人,亦可以为社会做到些事,亦感觉到在我可以为香港这个我出生的地方作出一些贡献。三十多年的政府工作我觉得有五点的体会,希望跟大家分享。
第一,就是沟通的重要性。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全香港人,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、要做得到位,那我们是一定要知道市民的生活、他们的需要,所以沟通是重要的,听他们的意见是好重要的。如何建立一个对话沟通的机会呢?其实都不容易,但若果做不到,好难将工作做得好。
第二点就是思考要用不同的角度。做政府的岗位,正如我刚才说,是不停转换,可以让我们有机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、思考问题。例如负责管钱的同事与负责「使钱」的部门的立场一定是不同的,大家都会尽力去争取达到自己的工作目标,理解问题的角度大家应该会不同。当我们有了不同岗位的经验,我们去到一个比较高级的位置时,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些判断。即是说,如像我们行上山时,可能因为太斜不可以直上去,那我们要围住山转上去。你即是可以以三百六十度的不同角度看了后,上到山顶当然会有较好的判断,你会知道自己当时的情况是怎样。
第三点我认为是重要的,就是团队。我一直相信,一个人是不可能懂得做所有的工作。政府的工作涉及全香港所有范畴,一个人无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。我不时会和我的同事说,其实我的同事不多,主要只有三个人。即使我比一个同事优胜,我也不可能比他们三个人的总和优胜。所以,我好多时要问他们的意见,要听取他们的意见,因为我认为几个人一定会比我一个人「叻」、懂得的事亦比我多。整个政府我认为都是一样,如何令同事能发挥(才能)、(让)制度有效运作,这亦是我很关心的题目。
第四方面就是取舍。在政府工作,每日都在处理不同的政治问题。我一直相信这一句话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」(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),什么时候坚持,什么时候协商,无一个标准,我们需要具体事情要具体讨论。政府的政策是要得到社会主流的支持,我们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。大家读书也有可能读过统计学,都知道「normal curve」是如何,社会就如这个曲线,像是一位肥胖的男士躺在地上,中间肚子位置是最大的,这代表是最多人的一群。政府是要得到主流的支持就要争取「肚子位置」这群人的支持,而不是其余的两极,所以当社会不团结,大家各走极端的时候,无论是经济民生都很难发展,很难改善。
最后一个,第五个,就是原则。要得到最多人的支持,民粹当然是一个方法,但政府民粹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,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,对长远来说一定是弊多于利。现在大家都能看到,例如希腊,因为多年前它也有民粹的政策,多年后问题就出现了。为了社会整体及长远的利益着想,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政府一定要坚持,我们是要择善固执,所以在寻求妥协的政治过程,当然要做一些「hard choices」,或为一些「hard choices」来做准备。但如果政府得到主流的支持,要做这些「hard choices」的时候,我相信过程会较为容易。上述这五点,我想纯粹是抛砖引玉,其实不只做政府,我相信这些对自己做人,或者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价值,我希望今日能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各位同学,在大学读书我相信是开心的,我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机会,好好享受大学的生活,做多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,特别是一些进入社会后做不到的事情,例如去外地生活一下、交流一下,这些是很难得的机会,接触多一些不同的事物和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,大家多一些交流,了解多一些不同人的看法,扩阔自己的视野,我相信这些对大家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今日的分享到此,或许我可以(回答)一些问题。多谢各位。
完
2016年10月28日(星期五)
香港时间22时27分
香港时间22时27分